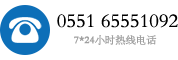基本情况
2014年6月12日,房地产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房地产公司将某办公楼及地下车库的土方、护坡、打桩、土建、给排水、暖通、电气等全部工程发包给建筑公司施工,约定合同总价1.2亿元。2014年8月,建筑公司与王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内部责任书》,约定王某为建筑公司第七项目部负责人,全面负责上述工程管理的各项工作,王某按照不低于工程款决算价的1%向建筑公司上交纯利润。上述合同签订后,建筑公司及王某进场施工。2018年9月4日,房地产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工程结算单》,载明工程审定额为1.07亿元,结算单加盖了建筑公司印章,王某在结算单上签名。2019年1月25日,法院受理建筑公司破产清算案,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后王某向建筑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总金额为2300万元,性质为普通债权,管理人经审查后对王某申报的债权全部不予确认,告知王某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确认诉讼。后王某未提起债权确认之诉,而是将房地产公司及建筑公司作为被告,要求房地产公司支付欠款2300万元,由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焦点问题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承包方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实际施工人是否还可以主张发包方直接向其偿还债务。
一审法院认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人直接主张工程款。从程序上讲,基于保护实际施工人背后农民工的生存权益的价值考量,从当前建筑市场秩序尚不规范的客观实际出发,司法解释赋予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直接主张工程价款的起诉权;从实体上讲,依然严格坚持合同相对性,要求必须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违法分包人的工程价款数额,且只能在该欠付数额范围内确定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给付责任;从结果上讲,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承担给付责任后,相应地消灭发包人与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也相应地消灭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从诉讼结构上讲,采用的是典型的“代位权诉讼”模式。
本案是在建筑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受理的,从表面上看只有一个给付之诉,事实上却包含两层诉讼,一是实际施工人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纠纷,二是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工程价款纠纷。如上所述,这是典型的“代位权诉讼”,实际施工人仅是“以自己的名义”代行建筑公司对房地产公司享有的工程价款请求权,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破产申请受理前,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起下列诉讼,破产申请受理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一)主张次债务人代替债务人直接向其偿还债务的……”及第二十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向人民法院提起本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所列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因建筑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程序本身即为债权实现程序,为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有序受偿,破产申请受理后,所有基于债务人财产的清偿均应当通过破产程序解决,而不得通过个案诉讼获得个别清偿,所以实际施工人只能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在债权不予认定的情况下应提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而不能直接对房地产公司提起具有代位权性质的诉讼。同时,建筑公司在实际施工人与房地产公司之间承上启下,对于前者,与之相对应的救济途径是债权申报和后续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对于后者,与之相对应的救济途径是提起对外追收债权之诉。进而可见,无论是破产债权确认,还是对外追收债权以及王某是否为实际施工人,均无法绕开破产程序。当然,破产管理人与房地产公司所结算的工程价款最终是纳入破产财产统一分配,还是确定归实际施工人单独所有,这依法属于债权人会议和破产管理人的职权或职责范畴,虽然本案从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但是倘若系争工程价款依法应当归实际施工人所有,那么实际施工人无论是通过直接起诉被告的方式实现,还是通过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来实现,结果都应当是一致的。因此驳回王某的起诉。
律师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第四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法律规定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的特殊权利,但在破产程序中,如果允许实际施工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就会造成类似单独清偿的情况,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根据《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进入破产程序之后,类似本案的代位权诉讼就应当不予受理。
来源:中国建设报